電影
這是一部法國劇情片,描述十九世紀末,巴黎軍政府第一作戰委員會宣判陸軍上尉艾佛瑞·德雷福斯 (Alfred Dreyfus) 叛國罪名成立,並且在軍校廣場,極其羞辱的儀式撤除他的軍階,移送法屬圭亞那監禁。陸軍中校喬治·皮克卡 (George Picquart) 接掌情報科,認為德雷福斯的叛國罪名疑似毒樹果實,尤其關鍵物證的瑕疵足以翻案,不過陸軍高層聯合壓制,命令,扒糞,降調,中校並沒有因此放棄伸張正義,在一次非正式會面時把消息透露給藝文界的朋友,文學家左拉願意撰文揭弊,於巴黎震旦報刊登’我控訴’一文,輿情浪潮迫使軍政府重新開庭審理…
‘J’accuse’ (2019),改編自英國知名作家 Robert Harris 的小說 ‘軍官與間諜’,Roman Polanski 導演,Jean Dujardin, Louis Garrel, Emmanuelle Seigner 主演。故事本身就是法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冤案 – 德雷福斯事件,官官相護,社會腐化,然後勇敢的人站出來伸張正義,電影版規規矩矩的再講一遍歷史故事,是一部老派作風的片子。
特別介紹:‘J’accuse’ 這部片獲得 2020 年法國凱薩獎最佳導演、最佳改編劇本、最佳服裝設計,2019 年威尼斯影展評審團大獎(銀獅)。

J’accuse (2019)
J’accuse/我控訴/An Officer and A Spy/軍官與間諜








小額斗內 小額大心
聽說骷髏去酒吧
點了一杯酒
和一支拖把
雨木觀後感
德雷福斯事件
Roman Polanski 導演作品,編、導、演都是高水平,確實精彩,不過精彩又怎麼樣呢?如果記憶可靠,這部電影引發爭議,凱薩獎揭曉最佳導演時,Adèle Haenel 離席抗議,憤怒的第一槍,那片森林當然是鳥獸散,貌似很多國際影人開始選邊站,但似乎只有反對的那一邊才是政治正確,準確的說,不反電影反導演,原因自然和他的性醜聞有關,而我在思考該如何描述這部片的觀後感,其實獨立文字工作者相對自由,本當暢所欲言,可是我不知道該從何說起,這種詭異的矛盾應該是初老症,以前不在乎的東西必須再三斟酌了。碰巧前幾天看到 Pierce Brosnan 接受衛報專訪,有關他卸任第七號情報員之後的得與失,類似小小回憶錄,我知道該怎麼說了。
‘J’accuse’,電影故事來自小說,小說源自法國近代史上的德雷福斯事件,左拉撰寫 ‘我控訴’ 一文,這位將軍失職,那位部長縱容,控訴名單包括法國陸軍滿天星,概念類似 ‘審死官’ 裡面的宋世傑,一告山西知縣,二告山西布政,三告廣州知縣,順便連八府巡撫一塊告,表示一件冤案隱含整個體系出了問題。
說到冤案,不公不義於是伸張正義,代代人都喜歡這樣的故事,德案屬於典型冤案,定罪的關鍵證據疑似毒樹果實,如果可以證明那棵樹無毒,翻案值得期待。
這件冤案的關鍵物證是一張字條,被告親筆寫下軍事機密發給德軍,他們說這叫外患罪,也就是戲劇最愛用的叛國,出門左轉搭船直送魔鬼島,關到有人想起來再說。我個人覺得片子描述定罪的過程很有意思,當時的犯罪鑑識專家貝蒂榮比對字跡,嚴格來說他是人類學家,找他比對字跡有點疑慮,也許一百年前就很流行斜槓,更別說本業相當權威,類似名醫治百病的概念。貝先生說得妙,我忍不住跟你分享他的調查報告,被告的字條放大一百倍之後,如同攤在科學的太陽下,陰謀無所遁形,被告使用描圖紙臨摹自己的筆跡,故意加了小變化,所謂故佈疑陣,看起來不完全是他的筆跡,其實就是他親手寫的,所以罪證確鑿,換句話說,如果字條上是被告的筆跡,他叛國;如果字條上不是被告的筆跡,他同樣叛國。
真實歷史也好,藝術創作也好,總之片子在這裡使用黑色幽默描述德案最關鍵的物證有瑕疵,那種哭笑不得的感覺,百年前出現過,百年後繼續發生。換個角度看,法庭上有這麼一回事,政治上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比對字跡是整部片最輕鬆的情節,畢竟這是一則嚴肅的歷史事件,甚至還有傳聞導演企圖借古諷今,抒發自己多年來的冤屈,自然不能從頭到尾充滿笑料。我個人覺得這份企圖可以在片子裡看到蛛絲馬跡,比方說一開場軍校官士兵全員到齊,罪人被帶到廣場中央,拆他的官階,拔他的胸章,斷他的軍刀,片子花了不少時間處理這些細節,百般羞辱一名軍人,換作一般市民,違反公司保密協定、競業條款之類的,離職時集合全體同仁,摔爛他的手機,拔掉他的識別證,還有門禁卡清脆的斷裂聲,我們自問,有必要羞辱成這樣嗎?依照這部片的政治意圖當然有必要,儀式做好做滿做全套,才能反映當事人承受多麼大的冤屈,換句話說,電影導演拍片為了澄清自己是無辜的,這一步就像一腳踏在門檻上,出門或進門很難說,但是表達幾十年來他很委屈,這一點雪白閃亮,他有資格,而且有才華這麼做,無獨有偶,這麼做能夠說服多少人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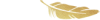
前任 007 Pierce Brosnan,我心中的末代情報員,還記得自己學生時代抱著十幾捲 007 影帶回家研究,應該找時間浣一浣他的春秋。
繳回殺人執照之後,Broasnan 演過一部電影名叫 ‘the Ghost Writer (2010)’,他演虛構的英國首相亞當·朗,醜聞,陰謀,戰亂罪,權力人物該有的祕密幾乎蒐集齊全,只差沒明講那在影射東尼·布萊爾。和本片十九世紀末的法國有什麼關係呢?同一位原著作者,同一位電影導演,所以那篇專訪有點離題又不會太離題,問了一下 Brosnan 與 Polanski 合作的經驗,然後圖窮匕見,如果十年後的現在給你選擇,你還會接拍波蘭斯基導演的片子嗎?他說當年是以電影從業人員的態度,好的劇本,有才華的導演,所以合作,十年前後大環境不一樣了,然而十年前後大環境不一樣了,現在要他選擇,答案是不知道。我想,這就是我看這部片的觀後感…
戲劇世界裡的勇者,情報長皮克卡,文學家左拉,伸張正義毫無懸念,他們沒有立刻送進巴黎萬神殿供後人瞻仰,還得過一段苦日子,逃到英國避難的日子,那都是伸張正義的代價,在這裡被淡化是可以理解的,畢竟好故事不必中肯,相信就夠了。而現實世界裡的勇者,但願上天眷顧,讓我們這輩子多得幾個吧,因為伸張正義就是良心發現,做一件事,愛一個人,忠於自己的意志,多麼美麗的童話啊,好像有選擇其實別無選擇,有時還得逆向選擇,因為最難的不是看得見的善惡曲直,而是看不見的環境,氛圍,社會觀感,主流意識,隨你挑一個講,這些無形的力量企圖直接或間接封殺一個人,就像彈指一樣輕鬆,比方說片子裡的陸軍中校,白天打冤案,晚上婚外情,既然站出來向太陽怒吼,很帥是吧?那麼隱私也一併攤在太陽下,祕密情人 Emmanuelle Seigner 一句現在怎麼辦,幾個英雄不氣短?又比方說就影論影,波蘭斯基導演的片子確實有水準,縱然現在看來敘事四平八穩,老派作風,但是注重故事本位,明星其次,也曾在好萊塢當過所謂的新派,如今面對 METOO 這樣的浪潮,如果有人像法國凱薩獎一樣給這部片三個讚,想像一下什麼下場,所以現在開始效法左拉嗎?我控訴主流意識追殺異端,我控訴社會觀感矯枉過正,不是這樣的,連我自己都想吐掉昨天的午餐。
我看到的世界是同捆的,凡事就愛綁在一起看,從來不是一碼歸一碼,不小心犯了同捆規定,直接退後卅碼,或者退到場外自己玩沙,於是偉人教我們該怎麼辦,要嘛媚俗,要嘛孤獨。你知道嗎,偉人是不會錯的,不過偉人的建議只會出現在小筆記本的邊緣,因為那是我們永遠到不了的境界,所以永遠需要被提醒。比起天涯海角,我嚮往到得了的地方,只有在認清世界的前提下,獨立思考才有意義,尊重伸張正義的人,哪怕明天進辦公室繼續看他被孤立,自己心裡留一盞燈,先烈就不算平白犧牲。接納自己的普通,妥協現實並不可恥,同樣在心裡留一盞燈,提醒自己潛龍勿用。就這樣把責任和疑慮推得一乾二淨,只為了保持清醒,繼續認得鏡子裡的自己,相信那些會發生的注定會發生,屆時已經最好準備,低調所以踏實,踏實於是幸福。(2020-07-10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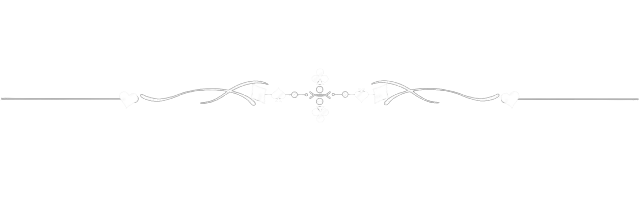

發表留言